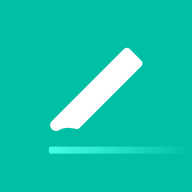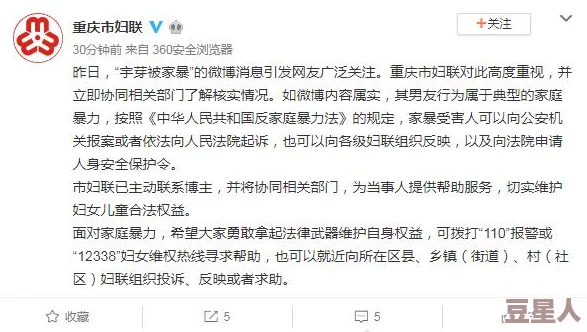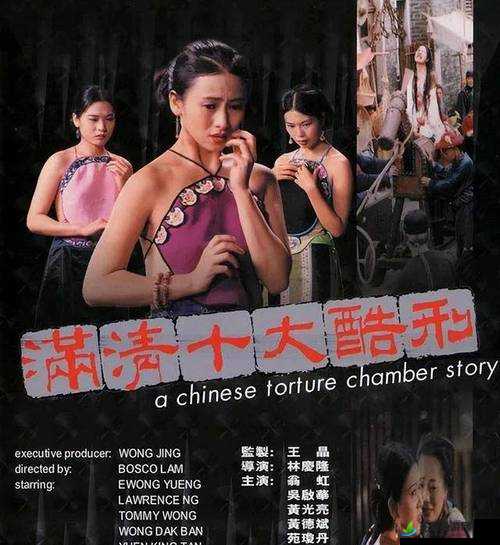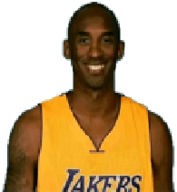英国当代作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Winterson)在《十二字节》一书中试图让我们看到技术如何改变人类的过去、现在以及正在到来的未来。如果我们的意识不再寄存在我们的肉体中,而是寄存在计算机网络上,那我们还算人类吗?如果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可以被彻底为人类服务的机器人伴侣满足,那人与人还会谈恋爱吗aaa
日本京都有着400年历史的古刹高台寺,2009年引进了一个名叫Mindar的讲经机器人。Mindar是弱人工智能(narrowAI),也就是说它只做一件事(讲经),每天只重复这一项任务。寺院计划更新这款价值百万的观音化身,使其具备学习能力,可以直接回应访客的提问。
物质与表象皆为虚幻——充其量是暂时稳定的,因此不要太过迷恋它们。而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它们是我们日常苦难与不幸的根源。
宗教信仰与人工智能领域有着不少交集,这一点让我很感兴趣。也许是因为宗教思想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未来格局全然一新的世界——AI使这个世界变为可能,同时不可避免。除去科技变革,我们对“人类”的定义也将改变。我们的位置、我们的目标,甚至是我们存在的形式,都需要被重新理解。
对于人类而言必不可少的物质形体,对AI而言却无关紧要。AI不像我们那样体验世界。拥有实体是一种选择,却不是唯一的选择——甚至不是最好的选择。
我想说明,我们试图研发的是“纯粹的人工智能”,即AGI(通用人工智能,一种可以处理多个任务、进行思考的实体,最终将变为具有自主性的存在),它能够自己设定目标、做出决定,而弱人工智能——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处理单项任务、完成单个目标(如下象棋、分拣邮件)的AI,只是不断发展的AI大军中的一小部分。
事实证明,智慧并不只寄存于生物体上(当然),意识有可能也是如此。
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智慧来自某个或某些超脱了肉体凡胎的存在,是他们创造了世界和人类。那些被我们视作“人类独有”的特质,在所有的神话和宗教传说中都并不属于人类,而是那些不具实体、生活在三维世界以外的存在赋予我们的。
随着人类走向更为混杂的虚拟和物质世界,“存在”与“不存在”的界线将不再分明。虽然过程缓慢,但可以肯定的是,分辨虚实将不再重要。物质将不再重要。
现实不是由零件拼装而成的,现实是由模式构成的。
这是既古老又新鲜的知识,是一种解放。没有构成物质的基本模块,没有核心,没有根基,没有任何坚实可靠的东西,没有界线。只有能量、变化、运动、相互作用、联结、关系。这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噩梦。
我们该从哪里说起呢?
我很想同时从两个地方说起。但很不幸,我只能逐一顺叙,尽管大脑最强大的能力是并行处理。目前,计算机的运算能力快得惊人,但仍然要按次序处理;人类的大脑则可以并行工作。人类不必变成智能系统,就可以同时处理许多不同的事情——当我们将感觉运动技能、环境意识、思考能力融为一体时,这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人类不必接受教育培训,就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喝咖啡、接打免提电话、注意路标、揣测伴侣的心思、回想某部电影中的场景、伴着音乐唱歌、观察天气情况、知道大约半小时后应该吃饭、决定走某条路——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同时完成。AI不能像人类一样同时处理多项任务或思考多件事情,至少目前还不能。
因此,我很希望自己能够开启“双屏模式”或者“四屏模式”展开叙述。
赫拉克利特/佛陀。希腊/印度。
赫拉克利特就是那个声称“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的哲学家。这句名言被印刻在了我们的集体记忆之中,因为它简洁明了、一针见血,像禅宗公案和数学等式一样准确。变化流动的不只是河里的水,我们自身也在发生改变。我们体内每分钟都有超过9000万个细胞在新陈代谢。所谓的“我”,是一个始终在变化的“未完成”的存在。直至肉体死亡,甚至死后我们也并未停滞——就算并不存在宗教上所说的轮回转世,科学技术或许仍然可以证明此言非虚。你会上传自己的思想吗?生理机制并不代表一切。
释迦牟尼是这样顿悟成佛的:他一连数年主动探求人世间的真义,又花了很长时间独修苦行,然后他坐在菩提树下,意识到所谓物质只是被构造出来的概念。他意识到,流动的现实不可能被框束在思维创造的固定类别里。这与我们对于事物的一贯认知截然相反,我们认为物质世界是平静泰然、界线坚固的,思维则不然;但事实上,是思维在艰难地冲破自身概念的禁锢,只有概念变化了,才会有进步。
赫拉克利特和佛陀思考了现实的本质,而在600年后,耶稣才终于出现,在水面上行走,把水变成酒——《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基督教信仰中的各种奇迹,包括圣母生子、耶稣死而复生,都应该被视为理解物质世界本质的线索。神秘的东方精神信仰始终明白量子物理学家所说的“存在倾向”,即我们体验到的一切并不是确定的、坚固的。身体、思维、物质都是如此。
古希腊人也明白这一点。
对于西方人来说,我们的科学和哲学思想都根植于古希腊文明。除了犹太教的影响外,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同样也离不开希腊思想,但希腊思想是变化的(并不是停滞的),其中有关“变化”的观点也一直在改变……
赫拉克利特教导我们,宇宙和宇宙中的生命处在永恒的变化状态——他称这种状态为“生成”(Becoming)。
在思想上与他水火不相容的哲学家巴门尼德,则认为万物的本质是“存在”(Being),即稳定不变,耶和华与真主安拉都应该存在于这种状态中。万事万物表面上在变化,内核却是不动不变的。
柏拉图试图调和两位前辈的看法,指出的确有“不动不变”的事物,但它却并不存在于人世,并不属于我们。他提出了“理念论”(Forms)。理念世界中有完美的马、完美的女人、完美的生活,它们是理想的图纸,但在我们这座“玩具城”中,一切都是粗糙的仿品。我们拥有关于“完美”和“理想”的意识,却无法在玩具城中将之实现。
这就是柏拉图反对艺术的原因——它只是对现实的模仿。鉴于现实世界就是对真实的理念世界的模仿,我们不需要艺术这种“模仿的模仿”。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充其量仅有娱乐的功效,只是供人取乐的东西;而往坏里说,它是一种危险的幻象。
这种看法延续至今。那些认为艺术(网飞电视剧除外)消失后,自己的生活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的人,大概普遍都这么想。柏拉图无法从“现实只是理念的影子”这种观点中跳脱出来,因此他不知道的是,艺术并不是对于真实的逃避,而是一种追求真实的途径。
艺术不是模仿,而是一种充满力量的角斗:我们努力让一个无形的世界变得有形。这个世界就在我们的头脑之中(我们甚至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但只有艺术让我们有机会触碰或瞥到那些可能是“本质”而非“影子”的存在。物理学追求的是同样的目标,只是使用的方法不同。
……
17世纪,牛顿基于“空间”(emptyspace)的概念建构了他庞大的世界观:在空间(虚空)之中,有不可分解的物质在重力的作用下不停运动。这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宇宙,其中大部分事物是惯性或惰性的。一切都是客观的、可知的、可以被观察到的。
时间位于空间之外,与之不相关。宇宙之中仍然要有一位上帝存在——牛顿本人是个虔诚的信徒,但他相信,上帝创造了一个遵循着严格铁律的发条机械世界。人类不是机械,只因为我们是被按照上帝的模样创造出来的。
牛顿是个谦逊的人,但他也有标新立异、乖张古怪的一面。他长期醉心于炼金术,这让许多科学家感到难堪,但这也恰恰说明,他不完全等同于人们固有观念中的形象,仅仅是一位机械论研究者。在1704年的专著《光学》中,牛顿如此发问:“难道重物和光不能相互转化吗?”
他所说的“重物”就是物质。根据炼金术的逻辑,物质之间可以相互转化——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趋之若鹜地用铅块炼金,尽管这种尝试从未成功过。不过这套荒诞不经的逻辑背后也有理论支撑:事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因为万物都来自同一件“原料”。
牛顿非凡智慧的绊脚石,就是他相信这件“原料”是“无生命的物质”。既然大多数事物是无生命的,上帝就必须像亚里士多德所设想的那样,成为让事情发生的原动力。
但大多数事物不是无生命的。组成物质的不是没有知觉、互不相关的立方体,它们也没有静静等待着被重力影响,以运动一段时间——然后再次静止。
爱因斯坦(1879—1955)钻研之后发现,物质(质量)根本不是无生命的东西;质量是能量。质量和能量并非互不关联,而是可以互相转化——这其实就是炼金术士们所说的,一样东西可以轻易转化为另一样东西。
E=mc2。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方程式。能量=质量×光速的平方。
笨重的物体和缓慢的速度——就是这些组成了我们所处的“玩具城”。对于我们这种“普普通通的东西”——对于这个我们生活其中、可察可感的日常世界,牛顿运动定律可谓绝对真理。然而一旦超出了“日常”的范畴,牛顿的范式就不起作用了——它不适用于宏大的宇宙,以及微缩的量子世界,但这个事实直到迈克尔·法拉第(1791—1867)和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1831—1879)开始研究电磁学,发现了电磁场之后,才逐渐显现出来。他们的发现动摇了牛顿学说的世界观——这并非故意挑衅,他们不是亚里士多德那种专爱唱反调的人;而是因为场论削弱了“无空隙的东西”(原子)和其所处“空间”之间的界线。最早的电磁场,例如无线电波和光波,都是被当作某种“东西”来研究的,然而爱因斯坦思考了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发现后意识到,当我们谈论“场”时,我们说的其实不是“东西”,而是交互作用。
爱因斯坦指出,物质不能与它所处的重力场分离。物质和空间不是相互独立存在的。没有所谓的满或空。
时间和空间也不是相互独立存在的。时空,合为一体。
佛教一向反对将自然现象看作独立的存在。佛陀的禅理是一种充满“联系”的观点——生命力存在于相互依存的网中。
在佛教徒看来,静止的现实是梦幻泡影。无常,即一切存在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是诸多佛理的基石和出发点。
这些事物(包括我们在内)并没有在等待着被某种力量影响,包括上帝的力量;它们自己就是力量,又与其他各种力量纠缠在一起。所谓“力量”,也就是能量。
佛教用“轮回”一词指代生命无休止的运动,对于佛教徒来说,这意味着一切都不值得执着和依恋——物品、人,甚至是我们珍视的理念。尤其是我们珍视的理念。这并不是对于生命的蔑视或疏离。连接至关重要,执念则不是。
连接。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对不对?
这当然是因为我们开始意识到连接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一张巨大的网。蒂姆·伯纳斯-李即刻领会到了这一点,知道自己无须再聘请广告公司为它命名。
连接从根本上不用依托硬件。谷歌的环境计算以及其最终想要实现的神经植入,目的都是在不依托硬件的情况下将我们无缝连接。不需要设备,不需要任何一件“东西”。
我们与他人、与某件艺术作品,或者与某次经历之间最强烈、最富有生机的连接是无形的(没有硬件介入),但这些无形的连接却是我们人生最坚固、最深刻的组成部分。
连接是一种关系模式——不是相互分离的数据仓库之间的连接,而是人与人之间再也没有真正的界限。
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道”“流动不居”,印度教则称之为“湿婆之舞”。无论冠以何名,连接都不是停滞的、被动的;它是动态的。
流动很重要。物性(对物体的依恋,包括我们对自身的依恋)只是水流之中的浮光掠影;是影子,而非实质。
佛教提倡正念,但什么是“念”呢?
勒内·笛卡尔(1596—1650),这位质疑人类一切知识根基(本质上是质疑权威)、质问我们如何才能获知真相的法国哲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思维(mind,又译“思想”“心灵”“精神”)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
标题:人机交互热议:AI能成为佛教徒吗?
版权:文章转载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